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(简称科大)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零四个月,从1958年8月底到1987年1月中。进入科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虽然相隔近三十年,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。进入科大时,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;我离开科大时,再次被开除党籍。而且,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分相似。
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,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,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会,进行讨论,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。充分讨论后,再付表决。若获通过,再呈报上级党委。批准后,才算生效。可见,开除党员一般是很麻烦的事。但是,党章上也规定,如遇紧急情况,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,不需召开党支部会,也不给予被开除者申辩的机会,立即执行。
所谓“紧急情况”,一般指的是是战争、火灾、大地震等时间尺度很小的事件。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,如果一个党员图谋不轨,容不得正常的开会手续。必须立即开除,才会动用这个特殊条款。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,都不是在战场上,当时也没有地震,而是在大学上课。可是,两次都是按“紧急情况”办的,即立即予以开除,没有开会,也没有申辩的权利。
我之所以有幸连续两次获得这种待遇,并不是由于我的地位特殊(当然,也不是一点特殊都没有),主要原因是,按阶级斗争理论,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。毛泽东曾说,“我们没有大学教授,全部用国民党的,就是他们在那里(指大学)统治”,“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,实际上是国民党。”也就是说,大学就是一个国民党占领区。在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军队后,大学就变成了消灭“国民党”的一个主要战场。就这样,我被“紧急”地消灭过两次。
这就是大学里的主旋律。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,是在1958年创办的。在我报到时,全校还只有一百多个筹辨人员,没有学生。办校的目的是,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量培养科技人才。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、导弹和卫星(简称“两弹一星”)的人才。当时中国发展“两弹一星”的计划,刚刚起步。
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院,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,甚至很少带研究生。因此,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,是个聪明的方案。科大最初的一批教授都来自科学院,不少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。所以,相对于中国徘徊不前的经济而言,这所大学的发展还算是快的。1980年开放后,去美国念物理学位的中国学生中,来自北大的最多,第二即科大,这是后话。我在科大,一开始是当一名物理助教。
科大创办的1958年,正在反右派运动之后,共产党鉴于大学的不佳表现,规定了更强硬的教育方针: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,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:“迎接这永恒的东风,把红旗高举起来……又红又专,亦工亦农。”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。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,有位元帅来参加,明确地说,科大应仿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——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办。科大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,即中共的国际党校,它的目的是培养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干部,它的学生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。
科大第一任校长,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。虽然,早在一零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,郭沫若就是出了名的诗人,但科大并未因他而产生诗气。事实上,此时郭沫若的诗也全是党“诗”了,我还记得一首:
郭老不算老,诗多好的少。
大家齐努力,学习毛主席!
反正,一切向毛主席学,绝不会有错。比如,1961年有一次正式传达毛泽东关于教育的指示,其中重要的一条是:考试时学生可以拿小抄。后来,在考场上,果然有学生根据这个指示,公开抄书,监考的教师只好佯装没有看见。
尽管如此,我还是很高兴来到科大。第一,无论如何,我有机会再研究物理了;第二,我可以脱离核反应堆,而去研究自己更有兴趣的课题。短短的人生,最愉快的事之一,不过就是能研究一点自己有兴趣的问题。至于“亦工亦农”,我一点也不害怕,打井、捉猪我都会,还怕其他?1959年秋,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“亦农”——到京郊的山上去种树。那个中午,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,成为全队之冠(也是我迄今最高的一顿进食记录)。可见我未忘农村,仍然是能吃也能劳动。
当然,这时的我,已经没有赞皇的赤膊与赤诚了(编者注:1957年12月,作为中科院近代物理所一名在反右派运动中“有问题”的青年科技人员,方励之被“下放”到河北省赞皇县,他不畏艰苦,努力劳动,获得当地农民认同)。在农村那八个月里,我还是极相信,只要经过努力的劳动,自己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,成为一个受信任的人。然而,党籍的开除表明,一切真心实意的努力都是徒劳。我明白了,企图给党中央写信一事(编者注:方励之的“问题”,是与北大老同学倪皖荪、李淑娴一起,在“鸣放”期间打算致信党中央,就团的工作提出建议。倪、李因此被北大定成右派分子),使我的等级发生了质的变化,被归入了另册(原出版者注:清代把户口册分为正册和另册。另册用来登记盗匪等坏人。后来用来比喻受到轻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人或事物)。就像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,一个人的等级,一经确定,就极难改变一样,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,一入另册(虽然它不公开写在身份证上),绝难有出头之日。任何努力,绝难得到承认。我不再幻想“经过改造”会再成为受到信任的人,事已不可逆转。青少年时代对共产党所抱有的天真和虔诚,就此消失殆尽。
“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,现在他又因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。”这句斯宾诺沙在被逐出教门罪时所说的话,也是我被开除党籍时的感受。
但是,我仍抱有一个幻想,共产党也许会有农民那种是非标准,至少对于一个安分守己勤奋工作的人,是容纳的。所以,我一直想,只要谨守认真工作这一原则,或许还是有我的发展空间的。
于是,我很努力地教书。对教书,我确也有兴致。
在科大的第二年,1959年,我就开始上课。几乎物理系的所有课程,我都讲过。从一年级的普通物理,到高年级的近代物理,从基础实验物理,到各门理论物理,我都教过。1960年,一门量子力学课,原由近代物理所的一位教授主讲。课到一半,这位教授有事离去。后一半课,由我去接上。学生虽然知道我还只是一个助教,倒也没有因助教来接替教授上课而表示不满,我对讲课更有了信心。
同时,我也开始做研究,我选择了粒子物理。研究条件很差。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期刊,欧美的出版物要时隔半年以上才看得到,更收不到任何预印本。周围同事中虽也有几个对粒子物理有兴趣,但也都是没有任何研究经验的年轻人,缺乏有效的讨论。孤立和闭塞是物理研究的大敌。困难虽多,但这终归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,所以,困难中也不乏乐趣。
1960年春,我开始投寄论文。初秋,我的一篇论文“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电核半径”被《物理学报》(Acta Physica Sinica)接受。当时《物理学报》的执行主编钱临照教授也在科大任课。一天下午,在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,他叫住我。他的面色喜忧各半。他先高兴地说,我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。接着,又有难色地说:
“不过,不能用你的真名发表,你是不是改个名字?”
很显然,这不是他本人的意见,也不是《物理学报》编委的决定。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没有用笔名发表论文的传统。
我知道了,我的行为(发表论文)已经开始超越了对另册公民所规定的可活动范围,因而受到限制。不准用真名发表论文,就是清楚地警告我:注意你的身份!我没有对抗的余地,只有接受。我立即想到的笔名是“方之”。初中时,我和哥哥合作(以他为主)写的一篇文章在报上发表时,就署名为“方之”。但,钱临照先生不同意,因为这两个字还是太接近我的本名。钱先生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位长者,所以,我就放弃了给自己取名的权力,请他代为取名。他答应了。
1961年第一期《物理学报》,刊登了我的论文,作者是“王允然”。看到这个名字,我对钱先生更尊重了。他用这一名字暗暗地诏告世界,在中国发表物理论文,除了同行的审稿外,还必须有王(者)的允许(允然)才行!后来,这个“允然”果然被明文规定,凡投寄《物理学报》的论文,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位进行政治审查,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,不予发表。我的第一篇论文,也即“王允然”那篇论文发表后,再投寄到《物理学报》的几篇论文,均被退回,皆因没有政治审查文件。不过,这些被退的论文并非无功,由它们作导因,钱临照先生与我渐渐建立了忘年交。













![[Full Album] Jin ( 진 ) - HAPPY](https://s2.save4k.org/pic/GF3n1qxdnaw/mqdefault.jpg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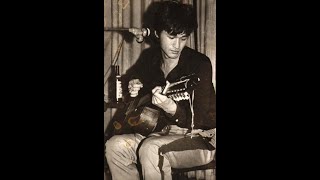







![TOP MIX MADO Summer Mix 2024🌴 Deep Feelings, Deep House Mix [MADO Music 2024]](https://s2.save4k.org/pic/XPFqZaV0hKg/mqdefault.jpg)


![[Супер Крылья сеасон 4 Сборник] Джетт | Супер Крылья TV | Супер Крылья подзарядка](https://s2.save4k.org/pic/Fkhy3cChiPA/mqdefault.jpg)
